[推荐]谁砍了柠檬树?
管理大師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誰砍了檸檬樹?
近年來積極關注全人類永續發展的管理大師彼得.聖吉,11月21日應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邀請來台演講訪問。被《BusinessWeek》推崇為當今最有影響力的管理大師之一的聖吉,長期以來致力推廣「學習型組織」,並在全球掀起組織學習熱,他的成名作《第五項修練》更被《哈佛商業評論》評為「最有影響力的管理著作」。
主持人高希均教授:這真是台灣社會一個空前的盛況,我們聚集了兩千六百多位朋友,大家要來聽彼得.聖吉博士的演講,以及他與張董事長的對談。今天下午這個盛大的聚會,也許正是台灣社會的一個轉捩點:
我們要把一個缺少和諧共識與願景的台灣社會,變成一個進步的、團結的、共享的「學習型社會」。在學習型組織裡,可以說真話,可以反省及深度匯談,可以接受別人批評,可以改進自己,可以培養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這不只是一個人的學習,而是團體的學習以及團體的實踐。
我們「天下文化」很高興從1994年起就先後出版了他的三本書(譯成七本),字數超過了一百六十萬字。即以他最著名的《第五項修練》而言,有三十萬字。這本書不好讀,但是只要耐心讀——任何一頁、任何一章,都會有收穫。
聖吉常常強調:1990年代以來,最成功的企業是「學習型組織」,因為企業唯一最持久的優勢就是要有持久的能力,比對手學習得更快。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的參與對談,更證明了「比對手學習得更快」是多麼重要!
但我不得不先做預警:學習沒有捷徑。一場演講不可能提供所有的答案,但會激發你邁向學習型組織。只要起步,就有可能。
聖吉:我今天不談太多基本的東西,而是要帶大家一起來思考學習型組織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對我們的個人、組織,還有社會、甚至全球所代表的意義。
事實上,原本我對於學習型組織並不熱衷,當我還是研究生時,我寫了幾篇關於學習型組織的文章,對我並沒有很大啟發。但是我對「系統」這個主題一直很感興趣,想要瞭解「系統」對我們有哪些深層的影響,生活中有許多核心問題,是大家從十七、十八世紀就開始探討的。
我常想,我真的不瞭解世界怎能有持續的工業成長,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源有限的世界,我們怎麼會有這種宗教式的信念,想要不斷成長呢?成長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一般人指的是經濟成長或是社會發展,政治人物在國家成長出現瓶頸時,會比較緊張,很多人想討論這個問題,也是因為他們沒有成長。對商人來說,他們(覺得)好像沒有看到利潤,這些關於成長的概念似乎和現實有所區別。
我在洛杉磯長大,成長經驗或許和許多台灣人不同。我四歲半時,父母搬到洛杉磯,我們住在聖伯納第諾山谷,我記得開車幾個小時,看到的都是整遍柳橙樹和檸檬樹,但是十二年後,這些都不見了;果園被暴增的人口取代。過去那裡是小孩子的天堂,到處都可以打棒球,但是現在學校有時還會建議小孩子在某些時段,不要離開家裡或學校,因為外面的污染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知道成長不只代表利潤,不只代表GNP,事實上,實際的生活經驗或許更重要。在1980年,我父母搬離洛杉磯,那時住宅區的房子每戶都加上鐵窗。我記得有一次我家遭小偷用大鐵鎚把後院的牆整個打垮,進去偷東西。你可以看到,一個從我小時候可以自由自在騎著腳踏車到處跑的地方,變成危險的場所,這樣的改變是非常大的,這對我來說又是什麼意義呢?
當然,沒有人故意要把世界變成這個樣子,沒有人想要把柳橙樹和檸檬樹砍掉,沒有人想要生活在鐵窗後面,沒有人預期到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就像沒有人想要讓全世界產生溫室效應或是讓全球貧富分配不均一樣。事實上,根本找不到一個人會刻意去這麼做的,所以,我們都存活在整個「系統」的現實當中,系統創造了這樣的社會。
我們現在擁有一百年前沒有人能想像到的科技能力,甚至可以改變世界,但是,我還是發現不只在台灣,在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一種無力感。真的沒有人想要毀滅物種,但是我們照現在的方式過日子,真的會毀滅很多物種。所以,我們必須談到「系統」,也許很多人要說,這不是我的錯,這是系統的錯,但在我們研究系統的人眼裡,卻不是這麼回事。
問題在於,我們如何創造這種互相倚賴的模式與系統。比如說,從小受虐的孩童長大後很可能成為施暴的父母,這不是電腦系統,也不是管理系統,而是一種互相倚賴的模式。文化就是一種互動的系統,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的小孩和一百年前的小孩還是有某些相似的地方。
近年來積極關注全人類永續發展的管理大師彼得.聖吉,11月21日應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邀請來台演講訪問。被《BusinessWeek》推崇為當今最有影響力的管理大師之一的聖吉,長期以來致力推廣「學習型組織」,並在全球掀起組織學習熱,他的成名作《第五項修練》更被《哈佛商業評論》評為「最有影響力的管理著作」。
主持人高希均教授:這真是台灣社會一個空前的盛況,我們聚集了兩千六百多位朋友,大家要來聽彼得.聖吉博士的演講,以及他與張董事長的對談。今天下午這個盛大的聚會,也許正是台灣社會的一個轉捩點:
我們要把一個缺少和諧共識與願景的台灣社會,變成一個進步的、團結的、共享的「學習型社會」。在學習型組織裡,可以說真話,可以反省及深度匯談,可以接受別人批評,可以改進自己,可以培養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這不只是一個人的學習,而是團體的學習以及團體的實踐。
我們「天下文化」很高興從1994年起就先後出版了他的三本書(譯成七本),字數超過了一百六十萬字。即以他最著名的《第五項修練》而言,有三十萬字。這本書不好讀,但是只要耐心讀——任何一頁、任何一章,都會有收穫。
聖吉常常強調:1990年代以來,最成功的企業是「學習型組織」,因為企業唯一最持久的優勢就是要有持久的能力,比對手學習得更快。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的參與對談,更證明了「比對手學習得更快」是多麼重要!
但我不得不先做預警:學習沒有捷徑。一場演講不可能提供所有的答案,但會激發你邁向學習型組織。只要起步,就有可能。
聖吉:我今天不談太多基本的東西,而是要帶大家一起來思考學習型組織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對我們的個人、組織,還有社會、甚至全球所代表的意義。
事實上,原本我對於學習型組織並不熱衷,當我還是研究生時,我寫了幾篇關於學習型組織的文章,對我並沒有很大啟發。但是我對「系統」這個主題一直很感興趣,想要瞭解「系統」對我們有哪些深層的影響,生活中有許多核心問題,是大家從十七、十八世紀就開始探討的。
我常想,我真的不瞭解世界怎能有持續的工業成長,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源有限的世界,我們怎麼會有這種宗教式的信念,想要不斷成長呢?成長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一般人指的是經濟成長或是社會發展,政治人物在國家成長出現瓶頸時,會比較緊張,很多人想討論這個問題,也是因為他們沒有成長。對商人來說,他們(覺得)好像沒有看到利潤,這些關於成長的概念似乎和現實有所區別。
我在洛杉磯長大,成長經驗或許和許多台灣人不同。我四歲半時,父母搬到洛杉磯,我們住在聖伯納第諾山谷,我記得開車幾個小時,看到的都是整遍柳橙樹和檸檬樹,但是十二年後,這些都不見了;果園被暴增的人口取代。過去那裡是小孩子的天堂,到處都可以打棒球,但是現在學校有時還會建議小孩子在某些時段,不要離開家裡或學校,因為外面的污染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知道成長不只代表利潤,不只代表GNP,事實上,實際的生活經驗或許更重要。在1980年,我父母搬離洛杉磯,那時住宅區的房子每戶都加上鐵窗。我記得有一次我家遭小偷用大鐵鎚把後院的牆整個打垮,進去偷東西。你可以看到,一個從我小時候可以自由自在騎著腳踏車到處跑的地方,變成危險的場所,這樣的改變是非常大的,這對我來說又是什麼意義呢?
當然,沒有人故意要把世界變成這個樣子,沒有人想要把柳橙樹和檸檬樹砍掉,沒有人想要生活在鐵窗後面,沒有人預期到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就像沒有人想要讓全世界產生溫室效應或是讓全球貧富分配不均一樣。事實上,根本找不到一個人會刻意去這麼做的,所以,我們都存活在整個「系統」的現實當中,系統創造了這樣的社會。
我們現在擁有一百年前沒有人能想像到的科技能力,甚至可以改變世界,但是,我還是發現不只在台灣,在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一種無力感。真的沒有人想要毀滅物種,但是我們照現在的方式過日子,真的會毀滅很多物種。所以,我們必須談到「系統」,也許很多人要說,這不是我的錯,這是系統的錯,但在我們研究系統的人眼裡,卻不是這麼回事。
問題在於,我們如何創造這種互相倚賴的模式與系統。比如說,從小受虐的孩童長大後很可能成為施暴的父母,這不是電腦系統,也不是管理系統,而是一種互相倚賴的模式。文化就是一種互動的系統,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的小孩和一百年前的小孩還是有某些相似的地方。
没有找到相关结果
已邀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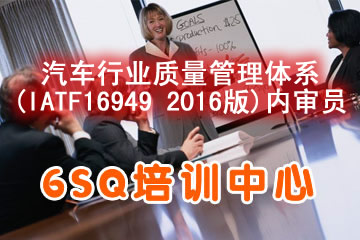




2 个回复
steventec (威望:38) (广东 深圳) 咨询业 咨询顾问 - 你来自云南元谋,我来自北京周口,握着你毛绒绒的手...
赞同来自:
我們人類和其他的物種一樣,每天相處就會創造出許多互相倚賴的模式,這就是所謂的系統。這並非新觀念,從人類有史以來就是如此,過去我們用文化這樣的字眼來形容,但是今日情況有所不同,現在有了一種新文化,叫做「工業文化」;這也許是第一種全球文化,深深的影響了人們在思考和行為上的模式,也用共同的觀點統合了全世界的人。
我第一次想到這個問題是在很多年以前,我認為我們生存在一個相互倚賴的網路當中,對我來說,沒有辦法真正地瞭解和影響別人是個嚴重的問題;我們世世代代形成了這樣的文化,如果大家都能體認到這個問題,或許情況就不會那麼嚴重了。
我曾經參加在維也納舉行的一個會議,研究系統思考的學者共聚一堂,當時有人說環顧全球看到許多飢餓與貧窮的問題,問題背後只有一個問題,就是在過去一百年內,「人類力量」成長的速度超出想像的範圍,但是我們的「智慧」卻沒有隨著「人類力量」而成長,所以如果我們的科技能力和智慧間的差距無法縮短,我們的未來就不值得期待。
因此,至少對我而言,這是我不斷在思考的問題,而我所創辦的學習組織中心,所要處理的就是這些根本的核心問題。不管從個人、組織或是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這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在一個大的組織當中,會有一些重要的團隊是需要學習的,同樣在我們的社會中,我們也要不斷學習。
特別是在過去二十五年當中,我有機會和很多跨國企業合作,一開始我並不認為我思考的問題和企業界相同,但是在一個現代社會中,企業是最有權力的。過去我們認為企業界在社會中最重要的功能是創造財富,可是對我來說,創造財富不是企業成立的原因,而是企業發展的結果。我認為企業最重要的功能是創新,包括科技的創新。要改變學校和政府是很困難的,相形之下,企業卻很容易創新,不斷有新公司成立,有潛力開創新的商業模式。
幾年前我有機會碰到一些企業界的人士,他們在社會上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就像在座的張忠謀先生(台積電董事長)一樣;他們不只重視企業的獲利,思考的也是非常深入而根本的問題。我還記得和當時摩托羅拉的執行長葛理芬(Christopher Galvin)吃午飯的時候,聊到小孩子的學習過程,他非常重視小孩子的教育,所以讓我瞭解到企業界還是有些有遠見的人,或許只占企業界的5%到10%,會去思考企業根本的核心問題。
就這樣,我對企業界漸漸開始有興趣。遺憾的是,我無法找到很多企業界的高層主管,會對上述系統性思考的議題感興趣,但我要再次強調,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社會上的公民,也會關心社會議題。
六年前,我們舉辦了一場會議,參加的都是企業執行長,我們成立了組織學習集團,而且後來發展出在MIT(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組織學習中心,現在已有十五年的經驗。我們和很多個人、組織合作,希望透過合作帶動系統性的變革。當時我們特別重視永續發展的問題,開會討論的議題包括產品所使用的材料以及全球溫室效應的問題。
2001年6月,我們邀請許多跨國企業的高級主管到波士頓開會,討論組織學習的問題,例如殼牌石油、英特爾、惠普、聯合利華等公司都有派人參加,那時聯合利華還不是我們學會的會員。很快的,我發現企業界有了一些根本的變化,我說的並不是全部的企業,也許只有5%到10%的企業,而且每個產業的改變情況也有所不同,像是石油和自然資源這類型的產業所受到的影響是最深的,它們真正有興趣的是工業生產活動對於自然環境的影響。
我們所討論的都是全球性的問題:如社會的貧富差距,全球的經濟相互依存度愈來愈高。當時有一位來自英國石油公司的人提到,我們不應該只討論數位落差的問題,還應該討論社會落差。五分鐘之後,一位殼牌石油公司的代表發言,他說當他們公司的經理人看到世界和社會現況,他們都很害怕。那時候,與會的每一位人士聽到一個跨國公司的高階經理人,使用「害怕」這個字眼,都感到十分驚訝。惠普的代表接下來又說,也許我們遲早都要重新定義,什麼叫「成長」。
經濟成長使我們用了太多原料,產生過多廢棄物,既然天然資源有限,這種情況勢必無法繼續下去。部分跨國企業公司確實看到這樣的問題,聯合利華的策略目標之一,就是讓他們的農業、漁業和消費產品永續發展,即使不賺錢也必須追求策略,因為重點不在賺不賺錢,而是要繼續生存下去。如果有一天天然資源耗盡,聯合利華就沒有產品可賣。
我們必須看到整個系統的運作方式。例如前一陣子網路的泡沫化,對於台灣和美國經濟都有很大的影響,經濟學家用泡沫這個字眼可以讓我們瞭解問題出在哪裡。生活在泡沫裡的人,觀念是截然不同的,這種投資是不切實際,而且遲早會有破滅的一天。那麼,如果工業時代是個泡沫結果會是如何呢?如果工業文化是個泡沫又會如何呢?
一切看起來如此合理,大家都知道同樣的經濟原理,說同樣的語言,我們知道如何創造利潤、管理現金流量,但是,這都是在泡沫中看到的情景。自然系統不會產生廢棄物,身為一個美國人,維持理想的生活所需,每週要用掉一噸原料,其中95%在使用過程中都成為廢棄物,例如二氧化碳,結果造成全球平均氣溫每年增加一度,這種情況還在持續惡化中,因為廢氣排放的速度,是二氧化碳分解速度的兩倍。
這些都不是新聞,但面臨這種情況,我們能做些什麼?就像剛才提到的,我們掌握科技的能力不斷增加,但同時又有強烈的無力感。事實上,這也正是我們學習所面臨的問題,學習不只是有新的想法,還包括了行動,大家都有這樣的義務和責任,去正視這些問題,我們都是地球的公民,如果我們不關心,還有誰來關心這些問題呢?